原标题:名家三棱镜·黄咏梅|荆亚平:小说的“后视”法与情感“放倒”术——黄咏梅小说论
荆亚平

帕慕克在谈及“我们阅读小说的时候,意识和心灵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时,曾有过一段诗意的描述:“我在年轻的时候阅读小说时,有时内心会出现一片宽广、深远而又宁静的景观,有时光线暗淡下去,黑白分明并且相互分离,各种阴影在其中涌动。有时候,我惊诧地感到整个世界沉浸在一种迥然不同的光芒之中。有的时候,余晖普照,含摄一切,整个宇宙化为惟一的情绪和惟一的样式。”[1]帕慕克是否有意强调“年轻”与小说阅读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不得而知。一个当下的事实是,我在阅读黄咏梅小说的时候,虽已不再年轻,却对帕慕克的这段文字产生了强烈共鸣。黄咏梅的小说令我惊讶的地方在于:同样是书写日常,为何她笔下的“俗世不俗”,能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倾听历史的回声”?为什么她如此执着于书写大时代下小人物们无所适存、无处安放的精神症候?她又是以何种视角于人们习焉不察的地方另有“所见”?什么样的小说技巧使她能将生活的沉重化为令人惊异心动的轻逸?她又如何借助写作过程中的真诚反思,确立起由“勇敢”走向“宽阔”的小说理想?
自2002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黄咏梅从事小说创作已经整整20年。在此之前,少女时代即因诗成名的她,一直以诗人之名立身。若从文学创作与空间的关系考察,黄咏梅的文学地理版图可戏拟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概括为:“问汝平生功业,梧州广州杭州。”当然,写作跨越的时间和空间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作家的成熟。小说与小说家的关系,恰如镜子与自我的相互映照,小说家借由小说而自我发现、自我确证。在黄咏梅不断发出“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我”的切问和审思的时候,答案也早已呈现在她的小说以及散见的创作谈中。
《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
彭发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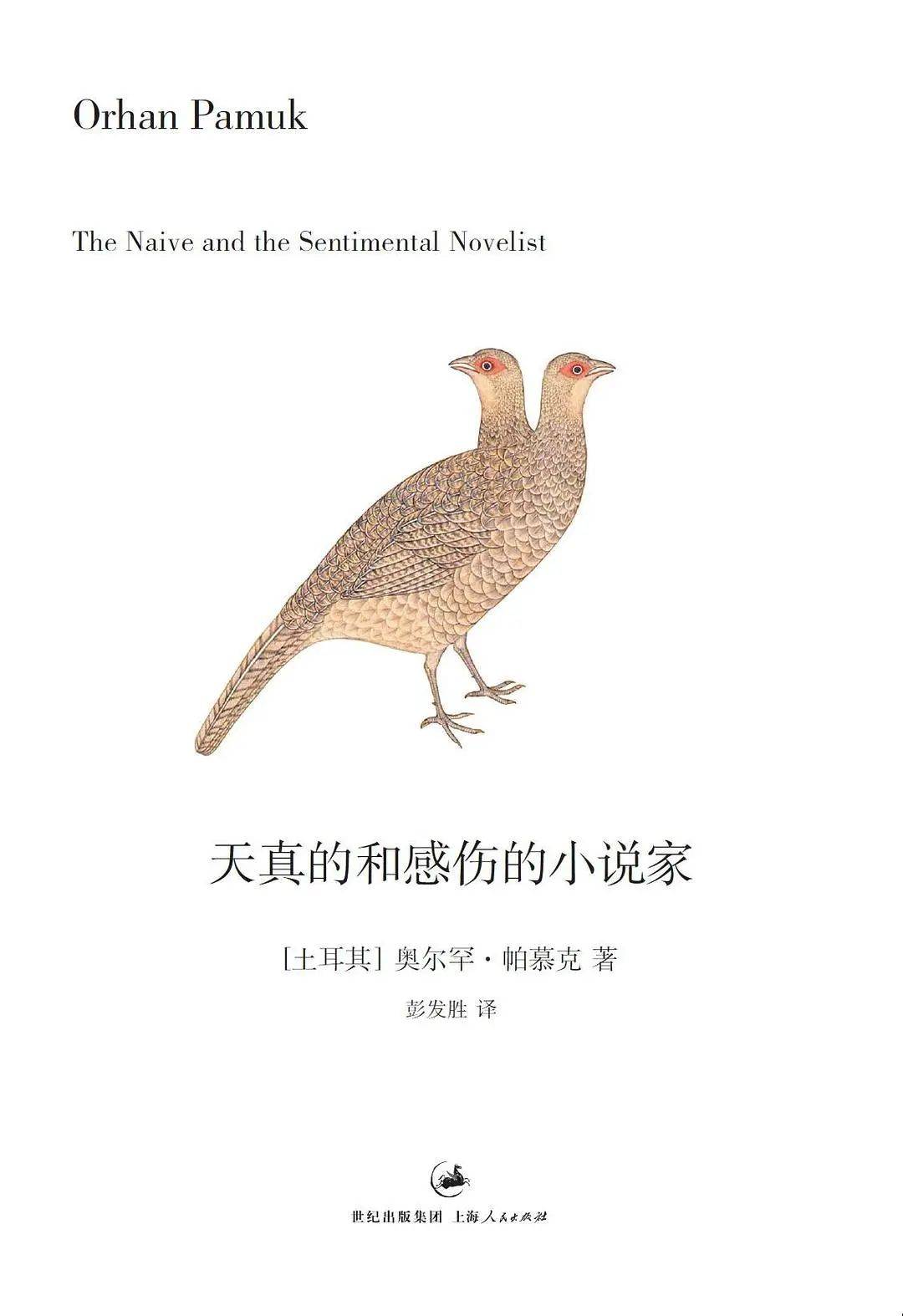
一
“后视”法:写作中如何“看见”
20世纪末中国文化(学)形态经历了由“共名”向“无名”的转向,60后作家以及此后以十年为期被命名的70后、80后等其他代际作家虽共处于“无名”文化(学)形态之下,在文学观念和追求上仍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即告别“宏大叙述”,走向“细小叙事”。个体经验、日常生活成为主要书写对象,甚至成为作家的自我宣言,70后作家黄咏梅就曾经明言:“与那些‘斗士型’的作家不同,我是个‘生活型’的作家。我在日常生活里寻找写作的资源和想法。”[2]
或许是早年在报社工作的原因,黄咏梅在消化素材方面,显示出“杂食”的一面。阶层分化、弱势群体、男女情爱、现代职场、网络游戏、粉丝文化、中年危机、老年孤独、克隆、传销、各类病残、文艺青年、赌徒、抹澡人、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纷繁世相人生百态,悉数纳入笔端。她赞许艾丽丝.门罗是“提着菜篮子捡拾故事”的作家,其实她自己同样是对生活保有观察和发现热情的作家。当然,“捡拾”什么故事,最后怎样呈现它,她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对于擅长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来说,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日常经常与‘俗世’这个词挂钩,所以,我觉得写日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将俗世写俗。没有情感、没有思考、没有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就很容易将日常生活记为流水账。”[3]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和警醒,在俗世里发现不俗,就成为黄咏梅的用心所在。
谈到在写作中如何“看见”,黄咏梅曾说道:“‘所见’在这个时代如此轻易,却让讲故事的作家几乎动弹不得。既难以在纷繁的‘所见’中辟出一条通往小说的蹊径,也难以在虚构的‘所见’中获得读者新鲜的目光。写作者在生活中到底还能看到什么?”[4]她对作家因“习见”而导致“不见”的麻木有着自觉规避,作为爱猫人士,她甚至“经常会顺着猫凝视的方向去看”,希望像猫一样“万事都觉得新鲜”。在从生活到小说的过程中,有人乐于拿着望远镜、有人习惯使用放大镜,也有人钟情哈哈镜,黄咏梅选择的是后视镜。她对生活的观察采用的是一种少见的“后视”法。无独有偶,詹姆斯·伍德也曾说过,当作家严肃地观察世界的时候,他们眼中呈现的是“持续退却的世界,是事物、对象和感觉迈向无意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探险从这种缓慢的退却中拯救出来;把意义、色彩与生命力重新还给大多数平凡的事物”[5]。
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可说是黄咏梅对“后视”法最成功娴熟的一次运用。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父亲,是个常年开着大货车奔驰在路上的男人。行驶在路上的父亲除了“前方的那团云”,根本没有机会从容赏景。某次为了欣赏雨后彩虹的停车,导致了交通事故,彻底终结了父亲的司机生涯。父亲用倒行健走延续着过往的身体惯性和生命感觉,结果却经历了人财两空的更大“车祸”。再也“搞不掂这个时代”的父亲最后迷上了在运河里仰泳,在成为岸上人们眼中一道奇异的风景的同时,也沉醉于“一用力,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的报复性快意。“后视镜”是小说里的一个重要意象,父亲固执地留恋“后视镜”里的风景,时代却无情地把他抛在身后,但恰恰是父亲的存在隐喻了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在不断加速前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美的欣赏、对人的信任乃至对生命的热情。早此一年完成的《小姨》则是“后视”法更为令人惊艳的一次亮相。小姨是一个精神停滞在理想主义年代,而肉身却不得不与消费时代周旋的女性。她的举止言行、思想观念都严重疏离于眼下这个时代,成为家人眼里“叛逆期永没过完”的异类分子、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反高潮分子”,只有心中埋藏的旧时爱情给了小姨一次鼓起勇气走进现实的机会,结果却是铩羽而归。此后,小姨成为一个与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叫板的“高潮制造者”,直到心中的理想主义激情白热化到极致,将她定格成一尊“自由引导人民”的肉胎雕像。时代把小姨和父亲甩在了一旁、身后,小姨和父亲也以自己的方式向时代发出了可能根本微不足道的一击,只是小姨比父亲爆发出更令人惊骇的生命热力。
“后视”法为叙事带来双重景深,一重是空间上的边缘(向两边看),一重是时间上的过去(往回看)。黄咏梅小说中的人物从未站到过时代的前沿和中心,父亲、小姨、少爷威威、契爷、达人丘处机、表弟、傅医生、阿甘、老蔡、抹澡人廖远坤……都是与时代脱轨、生活在别处(过去)的边缘人。“后视”还内在地蕴含参照的视角,“作家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岸,火车参照风景,对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6]。小说《档案》和《跑风》,正是以管山父亲、漂亮小媳妇为参照,映照出现代化进程中告别乡村进入城市者精神上的偏私冷漠。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后视”作为一种“回溯性观测方式”,拉开了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纵深感,前瞻与后瞩之间,恰恰构筑了生活的辩证视角”[7]。中心与边缘、个人与时代、日常与历史,当作家把握到其中匀称的节奏、呼吸,就会形成“小说的复调”,黄咏梅深谙这一秘密。所以她不会因为自己是“生活型”的作家而自惭形秽,她敢于质问“难道写当下就等于回避了历史?写日常就等于抛弃了意义?”[8],也更加坚定了从日常生活一点点写出“历史的回声”的写作信念。
《走甜》
黄咏梅
人间出版社
2015

二
“无力挽回的遗失”与“陌生拾到的惶惑”
黄咏梅曾经总结自己的写作说:“我就发现目前所写的小说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母题: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9]一个作家20年的创作基本围绕同一个母题,至今也还没有放弃的打算,这一方面说明黄咏梅有固执的坚持,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母题深刻地主导了作家的思想以及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不得不说,黄咏梅是拥有强大想象和虚构能力的作家,同一个母题在她的叙事万花筒里,晃一晃,摇一摇,总能变化出令人惊异的崭新故事。但我以为,黄咏梅真正想要写出的不是异彩纷呈的故事,也不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而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意绪。“我刻画小人物,不是对他们的遭际做细密的社会学分析,也不想选取知识分子批判的视角。我的小说更多的是呈现人物的命运,注意营造一种氛围,并真切把握他们的心境与人性的秘密,最终捕捉一种时代与人心的哀伤感受。”[10]黄咏梅像一个精神分析师一样,自觉地把“处理这个时代中人的精神事务”当作小说的责任。
从根本上说,“无力挽回的遗失”与“陌生拾到的惶惑”是一种现代情绪体验,是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得到的一笔额外“馈赠”。它从20世纪初甚至更早起,就开始频繁袭扰中国人的内心。在那些对人心的变化更为明敏,对人性的揭示更为精微的现代作家笔下,已经呈现出这一情绪的蔓延。它是鲁迅在《故乡》中发出的悲从中来的感叹——“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在《野草》中面对“将来的黄金世界”却“彷徨于无地”的自我预言;是沈从文《边城》中“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伤悼;也是张爱玲在“更大的破坏到来”和“来不及了”之间所体会到的焦虑。进入21世纪,这种现代情绪体验并不是减弱了,而是以更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变幻的形式影响着我们。也许,一个更令人悲观的可能性是,只要我们仍处于哈贝马斯所说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中,这种情绪就不会终结。由此来看,黄咏梅致力于表达的,其实是这一现代情绪在当下的赋形。这也是我们总是从黄咏梅塑造的诸多人物身上读出相似的精神表情的原因,她一直痴迷而反复书写的那一类人,在与时代的关系上,共有同一种情绪。
不少论者将黄咏梅笔下的人物称为卑微者与游荡者、后抒情时代的都市边缘人、时代的异质者等等,毋庸置疑,这些命名都精准地切中了人物的精神特质,但我却更愿意借用卡伦·霍妮的精神分析研究,将他们视为“神经症”患者。霍妮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11]霍妮是从社会文化而非生物病理层面鉴别“神经症”的,因而,她指出“神经症”患者最突出的两种特征是: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这两点在黄咏梅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他们或许正是因为在应对现代社会时反应方式上的固执,才成为无所适存的边缘人、游荡者;也因为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而成为心灵无处安放的卑微者、溃败者。我以为黄咏梅小说的意义,正在于刻画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写出了他们身上既无力又惶惑的普遍情绪。
黄咏梅对时代情绪的把握是从自我开始的,早期小说部分地有作者自我投射的影子。比如《路过春天》《骑楼》是为诗歌唱响的挽歌,“我”怀揣诗歌的梦想来到大都市,然而却无力应对“诗歌在这个城市没有自己的呼机”的窘境,“我”很快“掌握了一套话语”,成为“专为别人写好看的故事”的人,甚至以为“恋上柳其后,找回了我的诗歌”,殊不料终究只是柳其眼里那个“寄来两首诗和两瓣木棉花”的“傻B”。如果说“春天”是最诗歌的一种意象,那么“我”只能路过它,遗失它。《骑楼》里说“那个百舸争流的时代过去了,留给这个城市的,是一些美人迟暮的伤害”。这伤害也指向诗歌以及热爱诗歌的小军。城市用冷冰冰的现实将曾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小军变成了一个空调安装工,小军虽被高中少女重新激起了写诗的热情,但最终又“像一片纸一样从天上飘了下来”。对于小军来说,理想(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是二十三层楼的高度。
其后,黄咏梅日渐走出自我,塑造了许多应对时代变化的方式上十分固执、又无力与现实对抗的边缘人,比如曾经的东山少爷魏侠,已然无可奈何地成为年轻一代眼里的“大叔”,在跟年轻人的较量中只能落荒而逃(《少爷威威》)。武侠痴孙毅,固执地坚持读武侠,给自己改名为丘处机,然而现实中他却只是个菜场搬运工,既没办法帮助上访的“桃谷六仙”,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举步维艰(《达人》)。在城市里当保安的管山“开成鳖”顽强地要让女儿过上在城市里扎根的生活,最终却因为守护女儿的一次打架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女儿也不得不因此离开城市重回管山(《瓜子》)。契爷卢本(《契爷》)、小姨(《小姨》)、克里斯蒂(《献给克里斯蒂的一支歌》)、父亲(《父亲的后视镜》)、鲍鱼师傅(《鲍鱼师傅》)、傅医生(《八段锦》)、老蔡(《金石》)、满崽(《病鱼》)等,都是这个谱系中的一员。不止如此,黄咏梅有时也会赋予小人物某种异能或者病症,以略显夸张变形的方式来隐喻“我们时代神经症人格”的病态。比如嗜食者林求安(《暖死亡》)、有数字超能力的李小多(《单双》)、瘸腿的“大家姐”(《把梦想喂肥》)、肥胖症患者张明亮(《天是空的》)、癫痫病人“我”(《隐身登录》)、智障者阿甘(《负一层》)、丑人三皮(《三皮》),大麻吸食者(《带你飞》)、精神分裂者(《杀死王老虎》)等,这些“畸零人”的困顿挣扎是黄咏梅对“无力挽回的遗失”与“陌生拾到的惶惑”母题更为冷静极致的书写。
黄咏梅

三
“一笔,轻轻地将人的情感‘放倒’”
因为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寻,黄咏梅并不满足于那些读后只是让人觉得“惊奇”和“感慨”的小说,她要求小说要“动人”。她认为哪怕小说取材于新闻素材,也要“沿着这些已经发生的新闻,缓缓地,艰难地挺进,从新闻人物的内心逐渐进入到读者的内心,一笔,轻轻地将人的情感‘放倒’,将人们的冷漠、隔膜、躁郁、疑虑等情绪统统‘放倒’。这样的作品才动人”[12]。“一笔”而能将人的情感轻轻“放倒”,不仅需要一定的写作技巧,还需要有极高的小说智慧。因为“情绪奠定一个作品的主要基调,它决定了叙述的语调,以及你提到的一连串的人物心理、故事走向等等问题,但情绪又是最难找准的”[13]。黄咏梅的小说之所以总能在不经意之中打动读者,某些时刻又令人拍案叫绝,正在于这种“一笔”之间就将人物、读者的情感“放倒”的高妙技巧。
“放倒”首先必须是出人意表的,脱离既定的叙事逻辑,为故事提供一个新的方向,给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可能。《父亲的后视镜》里,父亲最后在运河里畅游时的那“一蹬”,他一生的不如意都在这“一蹬”里得以释放和补偿;《骑楼》里小军从23楼窗口的“一飘”,将他和诗歌的距离重新拉近,他得以“骑着自己的想象飞走”;《小姨》中,在游行队伍即将溃散的时候,小姨将身上宽大的黑色T恤“一撸”,以赤裸上身的雕塑之态捍卫了自己固守的理想主义激情;《负一层》中阿甘从负一层升到三十层顶楼的那“一跳”,终于实现了把问号挂到天上的梦想;《何似在人间》里最后一个抹澡人廖远坤河坝上那匪夷所思的“一掉”,实现了让河水替他抹澡,洗净了灵魂上路的最后愿望;《单双》里李小多最后面朝天空在路上的那“一躺”,以死的方式将胜券永远操在自己手里;《表弟》中表弟模仿雷克萨扑敌的那“一跃”,以游戏英雄的姿态退出了与这个复杂世界的赌局……黄咏梅往往是在故事即将走向结尾的时候才放出这“神来一笔”,但它不是我们熟知的“欧亨利笔法”,因为这“一笔”根本无从改变主人公的命运,并不会造成强烈的戏剧冲突效果。哪怕主人公最后走向死亡,也并不让人觉得惨烈和冷硬,反而透射出温暖的人性之光。“我喜欢写小人物,喜欢写他们在摆脱无望的现实纠缠时存有的高出地面一点的理想追求,这是他们进行自我攀升的重要精神支撑。”[14]这样的“一笔”里,有“高出地面一点的理想追求”,有黄咏梅对笔下人物的体恤和深情。
有时候,黄咏梅也会“一笔”让人物越过自己的性格和命运,于瞬间迸发出令人惊异的凌厉之势,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女性人物身上。对耿锵鞋垫上两对鸳鸯的“一瞥”,让乐宜从“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的“实习老婆”身份中醒觉过来,以一股风的速度对情人平静地说出“你该走了”,自己转身走进“人有我有”的婚姻生活(《多宝路的风》);总是把“是但”(随便)挂在嘴上的草暖,不动声色间就悄悄出头替丈夫解决了棘手的问题,在维护家庭安稳上,一点都不“是但”(《草暖》);许戈,名字里就有杀伐之气,兵不血刃摧毁了丈夫的婚外情,还“一笔”就“销毁”了与前夫的两颗试管婴儿胚胎(《睡莲失眠》);沈迪是一个被丈夫的谎言囚禁的女人,最后决定通过墙上的摄像头为自己做证,找回真实的自己(《证据》);樊花看透了生意场上的“勾肩搭背”不过逢场作戏,当有人僭越了这条线,要把樊花圈进他情感的私人领地时,樊花毫不犹豫就隐遁了(《勾肩搭背》);丈夫、领导眼里的“奇葩”米嘉欣,没有人能“看见”她的内心,借着旅行中的一次吸食大麻,她获得了灵魂飞翔的体验……这些女性不粘滞,有决断,身上都暗藏着一股“狠”劲儿,她们敢于对现实生活给以反手一击,虽然这些抗争可能依旧是无力的,甚至有时看似是在逃避,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抗争,夺回女性话语权这一行为本身,就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黄咏梅只用轻轻“一笔”,就为我们写出了女性突出重围主宰自我命运的一抹亮色。
“一笔,轻轻地将人的情感‘放倒’”,也为黄咏梅的小说带来轻逸峭拔的美感。黄咏梅一直深耕于短篇小说的天地,她对短篇小说的青睐,或许与早年的诗歌训练有关系。诗歌讲究凝练、精致、动人,而在黄咏梅看来,“一个精彩的短篇,就像一首被拉长的小诗,起承转合,很精妙的”[15]。可以断言,虽然黄咏梅后来放弃了诗歌创作,但她并没有放弃诗,或者说,诗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进入了她的小说。比如叙事上的充分节制,《给猫留门》以猫牵连起“华侨父亲”、老沈、沈小安、雅雅四代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背后是浩荡的历史风云和曲折的个人命运。黄咏梅把具有长篇小说容量的素材,剪裁成了一个类似于鲁迅散文《风筝》的“罪与赎”的故事。再如给出思考的留白,“我特别看重小说人物和故事背后的那些难以言说又意味深长的部分。故事是小说的基础,但一个能引人掩卷慨叹甚至自我对照的小说,不光是讲好故事就能达到的,还需要上升一些东西,需要作者的精神制造。大概跟我过去写诗有关吧,我喜欢用比喻和象征,即使再密实的叙事里也希望留出一些虚的部分,就像一个人,生活在众生喧哗中,要学会对自己沉默的那些部分进行反复思量”[16]。这是黄咏梅小说掩卷之后仍然耐人寻味的主要原因。卡尔维诺在论述文学中的“轻”时说:“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作出反应而去寻找轻。”[17]虽然黄咏梅也深知:“今天, 谁也无法给谁一个皆大欢喜的交代。”[18]但她却仍固执地在生活中寻找诗性,以各种变化的方式将主人公的悲哀化为忧伤,让痛苦得到安慰,她对笔下人物总是报以最大的善意和最深的理解。
《一本正经》
黄咏梅
凤凰出版社
2010
四
从“勇敢的真诚”到“宽阔的真诚”
黄咏梅是一个不断真诚地自我反思的作家,这使她的创作呈现出“生长性”的特质。有论者从她写作中的梧州、广州、杭州的地域转换来看待这种生长,也有论者从她的都市写作、“人到中年系列”“老年人题材”评价她的写作变化。但写作地理空间和题材选择的扩展,带来的更多是小说叙事表面的丰富性,并不能说明作家叙事能力的不断推进和提升。追溯黄咏梅20年间的写作历程,我认为她小说创作的“生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不断去“我”的写作。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黄咏梅发表第一篇小说《路过春天》的时候,用的是笔名“每每”,她后来说很害怕别人从小说里看到自己。早年涉及诗歌的几篇小说,可以看作是黄咏梅从诗歌转向小说写作时,对诗歌的一次次“回眸”。这一方面是她对诗歌“无力挽回的遗失”的忧伤,另一方面又是对即将展开的小说写作的“陌生拾到的惶惑”。但是很快地,黄咏梅找到了自己想要反复书写的主题——“写人跟时间的对抗,人跟欲望的对抗”[19]。她写各种小人物,无论是哪一种叙事视角(其中《填字游戏》较为特别,使用了少见的第二人称视角),越来越少“我”的影响,因为在黄咏梅看来,“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里,‘我’是小说的目光、情绪以及智力、能力,当然,‘我’也是小说的一个局限”[20]。她这里所说的“我”,除了指叙事人称,也可以理解为有限的个体经验。
摆脱了“我”的束缚之后,黄咏梅仿佛掌握了神秘的“读心术”,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有时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或者用她自己的说法,“写小说的时候,就是我心脏偷停的时候”,“我用偷停出来的时间,将自己当作不同的人,进入一个与自己肉身没有任何关系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得以跟一些隐匿的东西团聚,跟一些隐秘的内心活动窃窃私语”。[21]她写游荡于网络世界的表弟(《表弟》)、三皮(《三皮》)、王朝阳(《杀死王老虎》)、布杨(《关键词》)、“风中百合”(《隐身登录》)时,你会觉得她自己就是一个网上冲浪的高手,不仅熟知网络游戏规则,而且能洞悉各类网民的隐秘心理;她可以在两性身份和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之间自由切换:《档案》里的“我”俨然是一个典型的男性小公务员;《蜻蜓点水》让人疑心作者可能就是那几位老年男性中的一个;还有《普鲁斯特杨》和《小姐妹》中对不同年龄段女性情谊的描写;更不要说她对各种病态人格令人信服的刻画。即便是书写最可能见出“我”的女性,黄咏梅也多次强调:“在我的思维里,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或者视角,我的写作口味很驳杂,写我感兴趣的,写我能写的。我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雌雄同体的,相比‘女权’,我关注‘人权’。”[22]这种既热烈拥抱笔下人物,同时又“保持精神的冷”的写作姿态,决定了黄咏梅的写作由“我”出发而能渐渐隐匿“我”,朝向握着一支“人类的笔”写作的理想不断趋近。
其次是小说的结构由单线走向复调。黄咏梅早期的小说基本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由叙述人作为见证者直叙其事。从《契爷》开始出现了变化,小说设置了两个人物互为镜像的结构形式,虽然小说以《契爷》命名,但除了契爷之外,另一个人物夏凌云的形象也非常鲜明,甚至从小说的三分之二处开始,夏凌云一跃而为“高声部”,契爷则退为“低声部”,不仅形成了叙事的双重变奏,人物命运也在相互交叉映照之中各自发展。其后的中篇小说《瓜子》,叙事一方面沿着父亲“开成鳖”和“孟鳖”的“斗法”主线展开,另一方面是女儿“我”的成长经历副线,两者因为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而相互穿插,最终定格于女儿“我”从回管山的火车上跳下来的镜头。《病鱼》也通过在外面“捞世界”的女儿“我”和邻居的儿子小偷“满崽”的双线并置、交叉表现他们同是被命运狠狠改变的有“病”之人,甚至那条叫“满崽”的发财鱼也加入了叙事,构成了更为复杂的隐喻关系。《证据》中被丈夫圈在谎言包围中的全职太太沈迪,与鱼缸里的那条沈迪视为女性的蓝鲨互为镜像,蓝鲨从鱼缸的“越狱”也与沈迪最终要借助摄像头戳穿丈夫的谎言寻回自我形成呼应。《睡莲失眠》则以窗户为镜,将许戈的婚姻失败与对面窗户里女人的悲伤故事对照,许戈造访女人家里,透过女人的阳台看向自己家的一幕也别有意味,也许只有以他者为镜像,许戈才看清了自己婚姻生活的真相。《翻墙》中丧子的老年夫妻与隔壁年轻男孩相互映照。《蜻蜓点水》和《小姐妹》两篇则在结构上极为相似,老曾/老霍,左丽娟/顾智慧是彼此互为镜像的存在,黄咏梅借此将老年男性的身体欲望和老年女性的复杂情谊一层一层地推向高潮。这些复调结构的设置不仅扩充了短篇小说叙事的容量,还增加了叙事线条和层次的丰富性与立体感。
再次是隐喻的层次递进。受诗歌写作的影响,黄咏梅善用隐喻的方式联结和反映现实。比如以一个简单的意象来隐喻某种意绪,如《路过春天》《多宝路的风》《天是空的》《白月光》;用略带黑色幽默的命名隐喻某种现象,如《蜻蜓点水》《哼哼唧唧》《勾肩搭背》《把梦想喂肥》;再如《病鱼》《暖死亡》《睡莲失眠》《带你飞》《隐身登录》等指向我们时代各种病态人格的疾病隐喻;而《负一层》《走甜》《父亲的后视镜》则是对人生的某种整体性隐喻;还有频繁出现于黄咏梅众多作品中的各类“鱼”意象的精神象征意义。关于隐喻,黄咏梅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整部作品就是一个隐喻,对时代、人生的隐喻。从手法上来看,现实书写直接,隐喻表达含蓄,现实书写以精准的描写还原、扩充公众经验,隐喻表达则以超常的想象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漫游,二者共同创造出小说的魅力。当然,不同作家有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长处。相对于接受者而言,可能直接的书写更具冲击力,而间接的隐喻,则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心智去体会,就像有的酒,喝下去时感觉平和,但后劲十足,逐渐会在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奇妙的反应。[23]
虽然灵活多样的隐喻手法和层次递进的隐喻功能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但是也给黄咏梅的一些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带来了争议,比如《暖死亡》。但我以为,这部作品恰恰是黄咏梅创作中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对此,我赞同这样的判断:“《暖死亡》叙述是温吞的,而其隐喻和象征是尖锐的。对于当下中国城市经验的摹写,‘暖死亡’无疑具有世纪寓言的性质,这个短篇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我写近20年文学现象,一定会让短篇《暖死亡》进入文学史。”[24]20世纪末,贾平凹以长篇小说《废都》为时代画上了一个寓言的结尾,而新世纪的开端,黄咏梅则以短篇小说《暖死亡》为时代敲响了新的警钟。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用打造金蔷薇隐喻文学创作活动,希望从中探索作家“是怎样从这些珍贵的尘土中,产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洪流来的”[25]。倾心于短篇小说创作的黄咏梅也曾说过:“短篇小说在那么有限的文本里,从容地表现作家丰富的审美韵味和意境,就好像一片被压制得薄薄的透明的金箔,需要许多打磨的工夫。”[26]二十年来,黄咏梅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那个名叫沙梅的善良清洁工一样,日复一日地从尘土中收集金色粉末,熔合成金,打造出一朵小巧精致的金蔷薇。如果说沙梅的耐心和热情来自心灵的召唤,那么黄咏梅的专注和从容,则源于她对文学的真诚信仰。
《金蔷薇》
[苏]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
李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注 释
[1]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2] 黄咏梅:《“But”女士》,《锦上添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
[3] 黄咏梅、张鸿:《俗世不俗写——对话黄咏梅》,《走甜》,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236页。
[4] 黄咏梅:《“所见”之不易》,《长城》2020年第6期。
[5] [英]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6][13][14][15][16][23][26] 黄咏梅:《生活在喧哗中要学会对沉默进行反思》,《青年报》2018年9月16日。
[7] 曾攀:《当代中国小说的生活化叙事——以黄咏梅为中心的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8] 黄咏梅:《在日常生活中倾听历史的回声》,《锦上添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6页。
[9] 黄咏梅:《广州不是一个适合诗意生长的地方》,《南方都市报》2002年11月8日。
[10] 黄咏梅:《文学沦为边缘不着急》,《新快报》2011年4月17日。
[11]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12] 黄咏梅:《小说家不是旁观者》,《锦上添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页。
[17] [意] 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18] 张柠:《黄咏梅和她的广州故事》,《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
[19] 黄咏梅:《“时间”是我反复书写的主题》,《中华读书报》2020年10月21日。
[20] 黄咏梅:《写在〈档案〉十年后》,《长江文艺》2019年第9期。
[21] 黄咏梅:《偷停》,《锦上添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0、283页。
[22] 黄咏梅:《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雌雄同体》,《羊城晚报》2018年10月15日。
[24] 郭艳、黄咏梅:《冰明玉润天然色,冷暖镜像人间事》,《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4期。
[25] [苏]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李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
荆亚平
学林出版社
2009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目录
名家三棱镜·黄咏梅
黄咏梅|拍案,惊奇还是叫好?
张燕玲|偏偏喜欢你:人与文的人间烟火——黄咏梅印象
荆亚平|小说的“后视”法与情感“放倒”术——黄咏梅小说论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
邵 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框架、思路与方法
李平艳|多模态封面翻译研究——以英译贾平凹小说为例
乔 艳|贾平凹长篇小说英译的现状与变化(2011-2021)
梁余晶| “零距离”英译中国当代诗歌:问题与实践
张伟劼|从中国科幻到世界文学——《三体》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网络文学研究
陈 艳|女性易装与文学想象——论女性向网络小说中的女扮男装叙事
贾 想|沉浸体验、英雄叙事与虚拟物体系——论男频小说的RPG化
孔德罡|传统网文未曾实现的超文本文学形态——从《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浅谈当代网络“直播文学”
新作快评
刘志权| “秦岭”写作与中国本土小说之路——贾平凹《秦岭记》片论
丛治辰|洋装岂止是洋装 上海背后是中国——论禹风《大裁缝》
思潮与现象
李德南|期刊栏目主持人制的问题与方法——以《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曾令存|“对话”与文学史的“边缘化写作”——对舒晋瑜作家访谈的考察
张淑云|当代文学精神图谱的建构——论舒晋瑜的作家访谈录
作家作品论
王文胜|从几个关键词谈叶兆言抗日叙事中的创伤记忆
周红莉|王彬彬散文的两副面孔
姜 肖|“无穷的远方”与诗学的归途——李修文散文论
余红艳|时代人心与多元诗性叙述——论罗伟章《谁在敲门》
扬子江文学评论
邮箱|yzjwxpl2020@163.com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